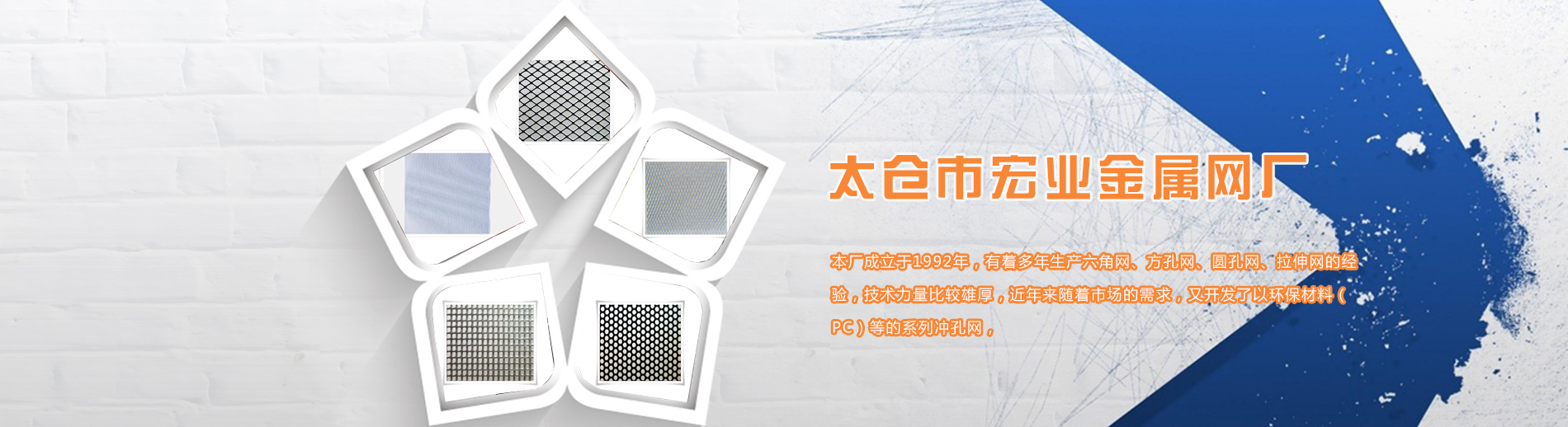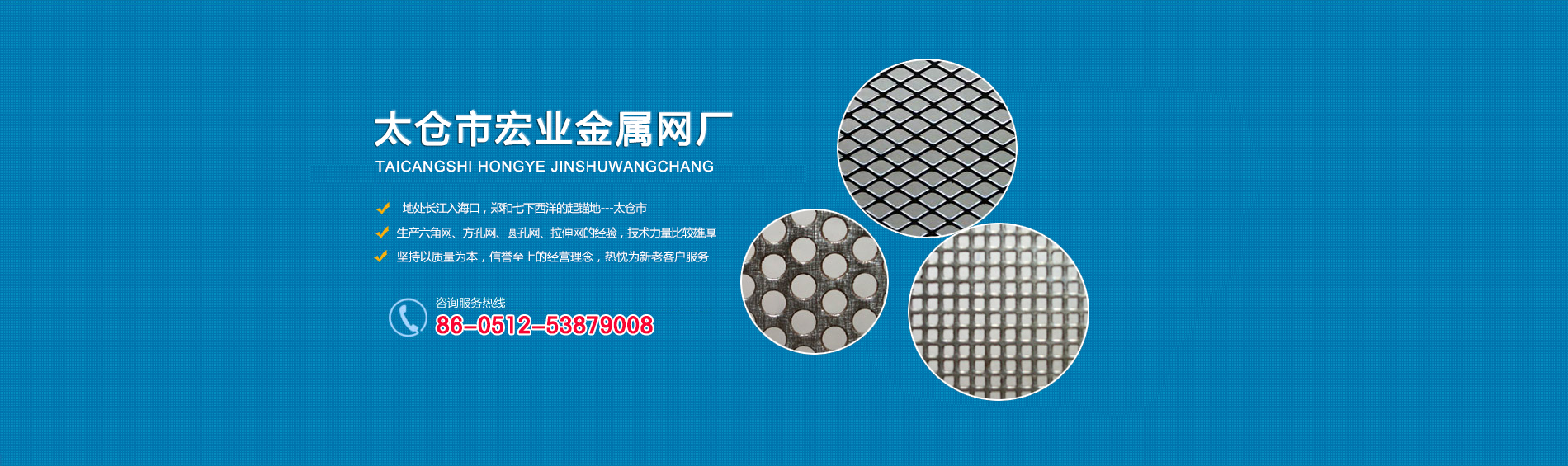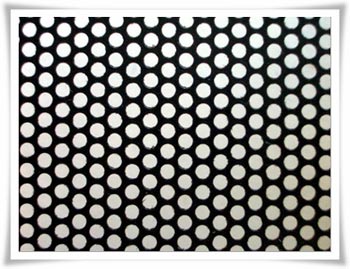高铁是一个超大型的工程,更是一届官员的政绩,而对于潘一恒来说,高铁只是他生前的最后一瞥。
2011年8月10日上午,7.23事故中D301次动车遇难司机潘一恒的追悼会在温州殡仪馆举行。前来参加悼念的有南昌铁路局、上海铁路局、福州机务段、温州市鹿城区双屿街道办的相关人员,以及潘生前的同学、亲友等100余人。
福州机务段段长傅伟奇在现场发言:“7月23日,甬温线发生了D301次与D3115次动车追尾事故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值乘D301次动车的我段动车司机潘一恒临危不惧,坚守岗位,忠于职责,不幸遇难。献出了他年仅38岁的生命。”
在高铁工程和体制中,动车司机的岗位显得微不足道,在列车控制示意图上,它只是人机接口处的一个操作点。而中国高铁之宏大却正如2007年初,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描述的那样:“古代能与之相比的是金字塔、空中花园、泰姬陵和长城,现代也就是曼哈顿工程、阿波罗计划和三峡工程了。”
这些庞大的工程有个共同点,就是所有身处其中的个体都是渺小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。而这些工程本身则像一个巨兽,有着与其他生命不同的发展逻辑。
复杂的列控节点
中国的高铁超级工程起源2003年3月刘志军接替傅志寰出任铁道部部长那一年。
傅志寰时代是许多老铁路人的怀念。“中国的天上飞波音,地上跑奔驰,但铁道线上要行驶中华牌机车,中国独立设计、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高速列车。”曾主持过4次大提速的傅志寰是中国铁路自主研发的坚定支持者。直到2003年,中国机车装备工业一直在“自主化”的道路上前进,虽然也有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,但始终掌握着产品开发的主导权。更为重要的是傅志寰在任期内提出了“网运分离”的铁路改革方案,这似乎预示着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就要炸掉了,而此时刘志军来了。
刘一上台就在铁道部内部作了一个报告,提出要创造“中国铁路的桑塔纳和奥迪”,后因表述肤浅,在公开传达时标题改成“跨越式发展”,其主旨是快速提升铁路运输能力和技术装备水平。与之相对应的是,在2004年1月,“刘志军倡导的《中长期铁路网规划》获得国务院审议通过。这一政策是刘志军指挥建设高铁体系这一超大型工程的蓝图。”一位接近铁道部的工程师说。而铁路体制改革的事则再也无人提起。
《中长期铁路网规划》要求在2020年前,中国将投资1万亿元人民币,建设时速200公里以上、总里程1.2万公里的“四纵四横”客运专线,即高速铁路网络;同时完成时速300公里以上高铁5457公里。而事实上,至2006年全球高铁总里程仅6400公里。中国的铁路客运专线(高速铁路)的工程极为浩大,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高铁网。也就是此时,张曙光豪言道:“曼哈顿工程主要是技术上的突破,三峡工程主要是工程上的突破,而中国的高铁将是在技术、工程和管理三个方面同时实现突破。”
“四纵”中的最后一纵就是从长三角沿东南沿海到珠三角的高铁线路,此次发生追尾事故的温福线就是其中的一段。2008年5月,为迎接温福线动车组开通运营,潘一恒报考了动车组司机,2009年6月取得动车组驾驶证。从参加动车组司机选拔考试、铁道部面试、西南交大理论培训考试到最后的实作培训考试,潘一恒都取得了良好成绩。
2009年10月,36岁的潘一恒当上了动车组司机。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,他不仅熟练掌握了CRH1、CRH2两种车型5种型号动车的操作技能,还成为了动车组的技师。
从业18年、安全驾驶列车238262公里的潘一恒非常清楚,动车车头上的人机接口的背后串联着一个庞杂“神经中枢”—列车控制系统,但他可能没想过这里面也藏着各种隐患。
2007年,中国铁路实行第六次提速,列车运行速度达到200公里/小时,此时,铁道部应用系统集成理论,建立了中国铁路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即CTCS技术体系。
CTCS分为0、1、2、3四级,前两级适用160公里/小时以下区段,后两级适用于200公里/小时和300公里/小时的区段。7.23动车追尾事故中两列动车均采用了CTCS-2级系统。
CTCS-2级系统由车载设备层和地面设备层组成,二者之间由轨道电路和地面应答器构成的点连式信息传输,实现地-车一体化。其中的ATP系统是负责列车发生追尾的核心部件。
ATP系统正常的情况下,如果前面有车滞留在闭塞分区内,后车将立即自动停车。7.23事故的第二天,两列动车的车载ATP设备的供应商和利时公司派技术人员至温州现场调查,据该公司称:“调查结果显示,车载的ATP运作正常。故障原因与路面控制设备有关。”和利时是国内最大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制造商,该公司的技术合作方为日本日立公司。